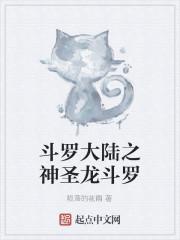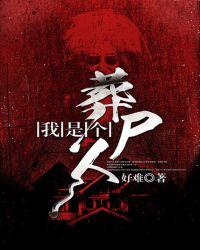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自序 人生几何(第1页)
自序:人生几何
据说,每个人一生的饮食习惯,九岁时就已经养成,南方人爱吃大米,北方人爱吃面食,都是在九岁之前形成的。不管生活环境如何变迁,即便是北方人去了南方,南方人来了北方,饮食习惯九岁之前形成定律,这个定律也将伴随人的一生。
不知道对别人咋样,对我来说,这个定律挺准。
1971年,我十六岁,跟随俺爹来到了开封。俺爹是土生土长的开封人,也是不到二十岁之前离家,四处漂泊。俺娘是四川人,少小离家,在西北与俺爹相遇,俩人结婚后从大西北到南京落脚,然后生下了俺们三兄弟……等于说,我们全家只有俺爹一个人属于面食定律,俺娘出生在四川,俺们三兄弟出生在南京,都属于九岁之前吃大米的定律。在我九岁之前的记忆里,俺爹就爱吃面食,在南京居住的那些年,俺爹每天下班回家,总要带回几个单位食堂的馒头。
来到开封已经半个多世纪,俺爹俺娘都已经归西,可我至今对馍依然不感兴趣,家常便饭基本以大米为主,这大概正印证了那个“九岁定律”
吧。来到开封后,馍出现在我嘴里最多的情况,就是在喝胡辣汤的时候,也只有在喝胡辣汤的时候,味觉才能感觉到馍香。
第一次喝胡辣汤的记忆,是在午朝门我堂姐家里。来到开封的头些日子,我住在堂姐家里,堂姐家是个大家族,姐夫姓傅,傅家兄弟八个虽各自成家,但都还和父母住在一个院子里。堂姐有三男两女五个孩子,家庭条件实属一般,五个孩子中除了最小的妞儿(五岁)不干活之外,其余四个孩子每天放学做完功课之后,都要帮着家里挣钱补贴家用,挣钱的渠道是纺棉纱和糊火柴盒。由于生活拮据,堂姐家每天吃大锅熬菜和芥疙瘩夹馍,芥疙瘩就是咸菜,馍可不是白面馍,是那种掺着高粱面和玉米面做成的馍。堂姐家的孩子们都很懂事儿,从没有跟我这个比他们大不几岁的三叔争抢过好面馍(白面馍)。我是从南方“大城市”
来的,受到堂姐一家的特别照顾。那年月的开封,每家的粮本上标注的都是百分之七十的粗粮、百分之三十的细粮,粗粮包括高粱面、玉米面、红薯面,细粮就是白面和大米。那时大江南北都有粮本,南方却没有杂面之说。来到开封,每一次吃杂面我都像被塞住了喉咙,肚里就是再饿,那些杂面窝窝头之类的食物,都是强咽进肚里的,杂面和好面掺在一起还好点儿,尽管是细粮少粗粮多,可那已经是一般家庭一年四季的家常饭了。
堂姐夫很会做饭,我说他很会做饭是因为他会把粗粮变着花样吃,今天杂面馍夹豆豉,明天杂面擀面条,后天杂面蒸包子。尽管我知道这是堂姐夫用心良苦想让我这个南蛮子吃好,可我内心还是接受不了那百分之七十的杂面。一天,堂姐夫对我说:“三弟,咱今个(今天)中午喝咸汤。”
起初我并没有在意堂姐夫说的咸汤是什么汤。晌午头,我学着孩子们的吃法,把杂面馍掰成一小块一小块泡进咸汤碗里,掌(放)进辣椒和醋这么一吃,顿时我的胃被刺激住了。这种刺激里携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让我一鼓作气吃下了两个杂面馍,被撑住了。堂姐夫满脸展样(舒坦,精神)地对我说:“说是咸汤,其实叫胡辣汤,胡椒太贵,冇舍得掌,开封人就叫它咸汤了。”
压(从)那以后,别管咸汤还是胡辣汤,都给我的味觉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它能让我多吃杂面馍。
1973年在开封上完高中以后,我上山下乡,去开封郊区一个农场当了知青。因为每天要干体力活,农场领导开恩,农场食堂不吃杂粮吃白面,我每顿饭基本上是俩白面馍一碗大锅熬菜,我的这个饭量算是农场女知青们的饭量,男知青至少要吃三个馍以上。因为能吃上白面馍,跟我一起种菜的男知青里面,有一顿能吃六个白面馍的,尤其是在农场食堂熬胡辣汤的时候,曾有人一顿饭吃进肚里九个白面馍。那年月,肚子里缺油水,胡辣汤利口,用开封人的话说,这叫“吃进肚里都是本”
。尽管农场改善伙食经常熬胡辣汤,但我始终觉得农场熬的胡辣汤不及俺堂姐夫熬的胡辣汤好喝。
两年知青生活以后,我跟随着回城打临时工的浪潮,回到城里当代课教师,先后去了四所中学代课,其中二十九中学位于相国寺后面,就是传说中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那个地方。撇开传奇不说,相国寺后面是一个最能体现开封市井文化的地方,尽管那时“文化大革命”
尚未结束,新时期尚未开始,但那里还簇拥着不少“黑市交易”
。有说评书的地下书场,有倒卖布票、粮票、缝纫机票和各种稀有票证的地下交易,还有偷偷摸摸倒腾各种吃食儿的。都说二十九中学是开封最差的中学,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所中学里的学生受市井烟火气影响太重,太社会。
相国寺后面有一家叫“王馍头”
的饭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家清末民初的老店,新中国成立后工商业改造时期归了国家。当时它是相国寺后唯一的饭馆,王馍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享誉开封的韭菜合子、炸酱面、鸡蛋灌饼,而是每天从早到晚支在店门前咕嘟着胡辣汤的大铁锅,除此之外,就是饭店里有个三十多岁可恶道(凶)的胖男人。胖男人经常跟食客发生矛盾,不是打就是骂,如果不是因为那一锅胡辣汤,我肯定不会去那家饭店吃饭,即使很怯气那个胖子,也挡不住那锅胡辣汤对我的诱惑。可令我奇怪的是,王馍头有那么好喝的胡辣汤,跟我同办公室的一位女老师却很不屑,每当我叫她一起去王馍头喝汤的时候,她只吃鸡蛋灌饼和韭菜合子,不喝胡辣汤。我问她为啥不喝胡辣汤?她说王馍头的汤不正宗,抽空她领我去喝“州桥胡辣汤”
,那才是正宗的胡辣汤。
女老师说的州桥胡辣汤店,在大纸坊街口的中山路上,是开封城里唯一日夜经营的饭店。女老师家住在大纸坊街,距州桥胡辣汤店很近。可说归说,一直到我结束代课生涯,要离开二十九中学那一天,女老师才领我去了位于中山路上的州桥胡辣汤店,就算是离开二十九中学最后的晚餐。那天也确实是晚上去喝的胡辣汤,州桥胡辣汤店里挤哄不动的人,那喝汤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前,我一直认为州桥胡辣汤是开封城里最好喝的胡辣汤,我坚定不移追随着它的味道,直至它搬迁至自由路。再后来,我与寺门义孩儿哥哥结识,被寺门的早餐拿住了我的胃,寺门回民的胡辣汤又成了我的最爱,州桥胡辣汤才渐渐淡出我的味觉。寺门对我后来改行文学的影响巨大,这与寺门沙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最终把我的生活方式改变成了穆斯林的生活方式,让我戴上了礼拜帽。
义孩儿哥哥是个吃家,我跟着他几乎把开封城里所有的清真胡辣汤喝了个遍,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产生了对胡辣汤进一步的认识。但这种认识还不是那种脱胎换骨的认识,直到有一天,义孩儿哥哥把香港新世界集团董事会的李长发先生领到我的面前,在与李长发先生聊天的时候,我才对胡辣汤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
李长发先生是开封人,1965年从寺门离开开封,那年他十九岁。李先生一生浪迹天涯,行商为生,在离开开封的大半辈子里,最让他念念不忘的一件事儿,就是想要搞清楚自己家族的来龙去脉。从小他就听老一辈人说,他们李家祖上是犹太人,是宋朝皇帝赐予来到开封的犹太人“七姓八家”
斗罗大陆之神圣龙斗罗
当神印王座中的最强王座与华夏神话中的五爪金龙共同穿越到了斗罗大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携带了21世纪的各种记忆,他是会选择名扬天下还是默默无闻欢迎加入花雨小屋,群号码258833709!现招群主代理一名,没有工资,没有福利,感兴趣的来,非诚勿扰!...
30条短视频助星球避开天灾
每晚9点更新,预收亲,要买金手指吗?劝你别惹金鱼脑求收藏,文案下翻可看!本文文案网瘾女青年秦若最近有个苦恼,她手机上的短视频软件颤音突然变成了盗版软件视谶。谶,作预言之意,语言的预言...
偏宠娇纵
作品简介江城的太子爷6衍泽位居高位为人极端利己与前任分手之后转身娶了苏城的第一美人韩嫣然。领证之前签了协议只谈利益不谈感情要钱可以要爱没有。剧场一办完离婚的那天晚上男人看着后视镜的女人一直盯着自己的车直到消失在拐角处回别墅后韩嫣然蒙着被子哭的上气不接下气如此狠心的男人。剧场二两年后再见6衍泽是在一场晚会上他作为6氏的掌权人出现一身剪裁得体的西装英俊的面孔举止尽显沉稳贵气。相遇拐角韩嫣然落荒而逃男人一刻没停留长腿迈步直接追上去。剧场三男人叼着烟靠在阳台上透过玻隔断门看着床上躺着的女人和儿子目光温柔如水一丝流淌在心尖的暖流原来太子爷也会有如此温柔的一面。...
我是个葬尸人
关于我是个葬尸人2o个考古系大学生,一次自认为安全的探险,没想到造成17人死亡的悲惨结局。一次意外,揭开了一个尘封了千年的历史迷案,南诏神庙,陕墓古葬群,滇国遗迹,埃及古国,一个又一个尘封...
扁栀周岁淮且以深情共此生全文免费阅读大结局
单项奔赴的三年,扁栀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笑话。所以,当欧墨渊让她在事业跟离婚之间二选一时,扁栀毫不犹豫的选择了离婚,从此她要做回那个理智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扁氏医药继承人。后来。前夫携全家老少跪求复婚。而商业霸主是她亲爹,扁氏二十三代国手医师是她亲妈,哥哥是黑白通吃宠妹妹无底线的黑腹总裁,弟弟是娱乐圈霸主。嗯还有个不好好在娱乐圈混就要回家继承千亿家产,眼高...
兽世最美雌性:多子多福生崽崽!
简介关于兽世最美雌性多子多福生崽崽!司鹿一不小心穿越到兽世,结果,绑定了多子多福系统,开启了兽世之旅!在系统一轮番的忽悠之下,司鹿燃起来了!生生生!兽夫这样好看,质量如此优质,那必须不能放过!...